林中泽评论《双城史》从巴比伦到法兰克-鄂图的“王国转移”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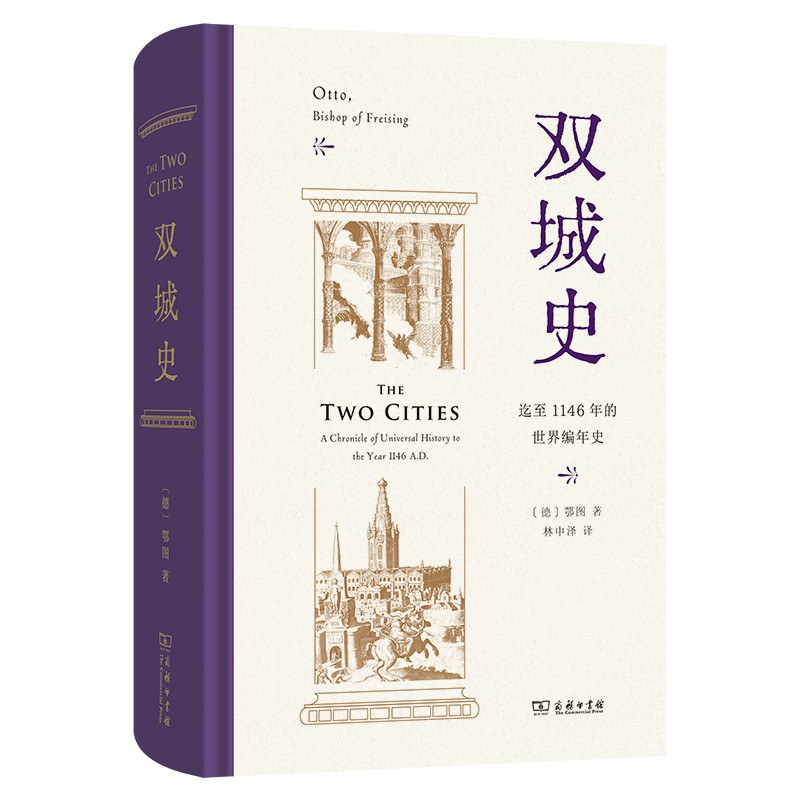
《双城史》,[德]鄂图,林中泽译,商务印书馆将于2024年9月上市。
鄂图,弗赖辛主教( 大约1114-1158年)的《双城史》是历史上第一部真正以哲学的形式对人类历史作品进行理论解释和系统解释的作品,因此一直被视为历史哲学的开始。从那以后,这部作品对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以至于神学家、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在启蒙运动之前都不得不或多或少地从中获取资源和灵感,并引用其中的段落或文字作为自己立论的权威理论。由于其独特的学术地位,西方学术界一直非常重视它,研究作品层出不穷。然而,它似乎在中国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这是一个缺点。这个翻译的出版,就是为了稍微填补一下这个缺点,以引起国内同事对这个著名内容的兴趣,并达到促进进一步研究的目的。
诚然,“双城”的思想,最初来自于700多年前距鄂图的早期拉丁教父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早就在《上帝之地》一书中提出,虽然上帝之地与世俗之地是对立的,但后者并不是一切都是坏的,教会和国家也不是完全抵抗;世俗的国家也是上帝所需要的,信徒应该在惯例中服从它。同时,它也应该受到保护和指导。然而,世俗的土地或国家最终会灭亡,并逐渐被上帝的土地所取代。因为奥氏通过简要描述历史的发展过程来分析双城关系,所以有人认为它应该被视为最早的历史哲学作品《上帝之地》。然而,奥氏的整个叙事过程充满了神学意义。他的主要目的是反驳当时非常流行的基督教亡国理论,并论证上帝意志对历史和现状的关键作用,尤其是未来人类命运的关键作用,而不是通过系统的历史叙事来总结人类历史进程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因此,虽然奥氏的《上帝之地》有着历史哲学的雏形,但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哲学体系,无疑是鄂图创造的。
对奥古斯丁上述相关双城的基本理论和观点,鄂图大致予以肯定和借用和继承。然而,由于历史环境和个人遭受的巨大差异,两位作者的思想观念不可能大相径庭。更何况鄂图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奥古斯丁的理论。首先,在奥古斯丁时代(5世纪上半叶),罗马王国的两件物品都处于外国入侵和内部动荡的双重压力之下,尤其是西方王国更接近崩溃的边缘。因此,当时的人们(尤其是基督徒)有理由相信世界末日即将到来,奥古斯丁有理由期待世界之城的分裂和上帝之城的到来。然而,在鄂图时代(12世纪初),我们不仅发现世界末日还没有到来,而且看到世俗国家通过群体流动和政权变化的方式完成了统治权力的更新和延续,其终点似乎不可预测。所以鄂图必须对这个历史演变过程做出新的解释。
其次,在奥古斯丁时代,基督教的合法性刚刚得到认可,政治和教育的关系相对简单。而且奥古斯丁本人出生在草根阶层,与当时的各种普通政权几乎没有交集。因此,奥氏可以从纯理论的角度充分发挥政治和教育的关系。而且鄂图的时代也不是这样。那时政教关系已经发展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加上鄂图本人既出生于皇室,又担任神职,是弗赖辛城的主教。这一多重身份使他不得不经常小心翼翼地在皇帝和教皇之间取得平衡。有人说,他曾亲自协调过自己的表侄皇帝腓特烈一世与教皇哈德良四世的争端,使他们和好如初。总而言之,在政教激烈争端的过程中,他总是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因此,在他的作品中,虽然他的用词相当含蓄,但我们不难看出,他有时指责皇帝过于贪婪,有时批评教皇过于贪婪。

鄂图的雕塑
《双城史》共有8卷,其中第1-5卷是对前人类似内容的高度概括和总结;第六卷和第七卷系统详细地描述了查理曼王国分裂至作者时代的历史进程、复杂的政治教育关系和地缘政治变化,因此具有特殊的创造力和历史价值。其中,从第7卷第12章到第8卷,叙述的内容是鄂图同时代的事件。这些事件要么是他自己的经历,要么是他当时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它们的价值特别高。然而,既然查理·克里斯托佛·米罗斯·米罗斯(Charles Christopher Mierow)在他的导论中,王先生已经对他进行了相当生动和具体的评论,我就不再赘述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想对鄂图在这本书中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思想和观点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首先,鄂图认为,凡俗势力也就是地上之城的兴起由弱到强,由强到衰,甚至最终走向毁灭,被上帝之地所取代。这个想法无疑是从奥古斯丁那里继承下来的,不同的是,他提出了著名的“王国转移”理论。在他看来,凡俗政权通过所谓的“王国转移”从一个群体转移到另一个更强大的群体;罗马王国是最后一个最强大的凡俗王国。这种传统观念没有改变,但在西罗马王国灭亡后,帝国的权力逐渐转移到法兰克人手中。8-9世纪之交,随着拜占庭皇位为女王艾琳,(Irene, 797-802年到位),查理曼被盗,(Charlemagne, 在罗马加冕的800-814年,帝国的权力中心从东部回到西部,所以法兰克人王国是罗马帝国的合法继承人。因此,鄂图在不削弱人们对上帝之城的热切期望的情况下,为历史发展的现实进程找到了合理的解释。
其次,与“王国转移”理论相对应,鄂图认为人类的智慧起源于东方,然后逐渐转移到西方,最终在西方结束。他明确告诉我们:
虽然人类所有的力量或智慧都起源于东方,但它们已经开始在西方达到极限。.....人类的力量...从巴比伦人传给米底人和波斯人,从波斯人传给马其顿人,然后传给罗马人,再传给罗马名义下的希腊人...[最终]从希腊人转移到生活在西方的法兰克人...(第五卷序言)
在实际叙述过程中,鄂图无疑将中亚和巴比伦视为人类心智的最初起源,以法兰克人为主体的神圣罗马王国将被视为人类思想汇聚的最后场所。在他看来,琐罗亚斯德教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心智的开始萌芽,然后是亚伯拉罕、摩西等犹太人的领袖和先知。随后,苏格拉底、柏拉图、西塞罗和塞涅卡等异教智者相继出现,其中所有的使徒和基督教教父最终出现。值得称赞的是,他并不局限于对这些人类心灵进行简单的时间排序,而是相信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即后来者对先在者有着一定的传承、发展和抛弃关系;这种思想显然对后来文明史观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三是鄂图认为,罗马世界帝国的统一为基督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和基础。他特别提到,房屋大维元首制度的建立,使罗马世界在单一政权的控制下,经历了100多年的纠纷,获得了真正的统一。这种统一与随之而来的相对和平局面的形成,不仅给人们的物质条件带来了好消息,也在创造每个人的精神福音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即基督的到来和基督教的诞生。这种观点之所以特别有价值,是因为它把基督教的崛起放在了罗马世界历史转折点的背景下。毫不犹豫地主张罗马的统一与和平有利于基督教的发展和教会的工作,这与历史现实非常吻合。虽然我们可以在尤西比乌斯的作品中隐约看到类似的观点,但像鄂图这样公开为罗马元首唱赞歌的例子在以前的历史学家中是很少见的。
第四,鄂图虽然对上帝之城的到来充满信心,就像中世纪其他神学家一样,但他对凡事的基本态度普遍悲观。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见证了太多的时代磨难,尤其是政教纠纷。在他理想中,政教关系应该是分工合作,相互表里,极其和谐。但常常事与愿违。皇帝和教皇的不断争吵,使他不胜其烦。再加上他参与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失败经历,使他感到更加沮丧。所以,他似乎对大多数人的获救没有太大的希望。到了末日审判的那一天,到底有多少人能得救上天堂,享受永福?还有多少人会被诅咒下地狱被永罚?鄂图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众所周知,奥利金曾经提出过“普救论”的观点,认为所有的人,甚至包括堕落的天使,也就是魔鬼,最终都会得救,但这种观点很快就受到了谴责。奥古斯丁以预定论为基础,认为只有少数被选中的人被拯救,而大多数人注定要受到谴责,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弃民。考虑到奥古斯丁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历史地位及其对鄂图个人的深远影响,从鄂图的实际叙述中综合考虑,更可靠的观点应该是,他至少不是奥利金式的普救论者,而是一个“部分救援”论者。对人性而言,鄂图似乎也不太乐观,他常常指责人们的贪婪和欲望是造成灾难的根源。从他的指责中,我们基本上可以初步推断,鄂图认为世界上的邪恶比善良更多,这与后来的笛卡尔、莱布尼茨等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双城史》第八卷,也就是最后一卷的相关内容。本卷系统地描述了人类历史的最终结局。人类最终到底会去哪里?对于一些以形而上的高尚生活为终身追求的上流社会或知识分子来说,这可能并不是特别重要;但对于普通信徒来说,这是一种利益。因此,通过鄂图这一卷对来生生活的描述,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中世纪旺期基督教世界广大民众的信仰关怀和愿景。虽然新约的《启示录》集中讨论了末日审判的场景,但它的代表意义太强了。单从字面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普通读者根本无法打动文化程度低的人,所以鄂图的系统解释是非常必要的。至少,鄂图以更直白的方式解释了《启示录》和《圣经》其他经文中第二次死亡、复活、审判、涤纶罪、炼狱、天堂的具体场景以及每个相关阶段,并巧妙地拼接了断环,以适当地协调相互矛盾。他继承了基督教世界长期流行的涤犯思想,为那些被原罪污染但从未犯过任何现罪的死亡婴儿设立了清理地狱入口处原罪的地方。虽然这个地方最终会随着审判的结束而消失,但它也为不久后“炼狱”的概念提供了重要的雏形和基础。
正如米罗先生所说,鄂图是一位谨慎而有判断力的杰出历史学家。他的声誉赢得了古代和现代学者的一致好评,他的神学观在16世纪被认为是正统的。在写作体裁方面,他继承了教会史鼻祖尤西比乌斯所创造的普通历史和教会历史的叙事套路,并有所发展,这使得他的作品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写作风格上也成为了与古代相连的历史杰作,与现代相连。另外,这本书文字流畅,词句优美,是一部兼具学术性和易读性的优秀作品。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版权归原创者所有,如需转载请在文中注明来源及作者名字。
免责声明:本文系转载编辑文章,仅作分享之用。如分享内容、图片侵犯到您的版权或非授权发布,请及时与我们联系进行审核处理或删除,您可以发送材料至邮箱:service@tojo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