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荣新江《大漠丰碑:出土文献所见西域史地》的三重关键
近期出版的《大漠丰碑:出土文献所见西域史地》,汇集了荣新江教授四十余载学术生涯中的三十余篇论文,内容涉及西域史地、敦煌吐鲁番学、边疆民族史等多个研究领域。通常来说,论文集的出版能为读者省去查找零散论文的麻烦,像知名的Variorum Collected Studies丛书便是基于这一初衷诞生的。不过,对于有着整体学术规划与宏观思考的学者而言,若孤立地阅读其单篇论文,虽能了解具体的研究成果,却难以把握其学术思想的整体脉络。从这个角度看,论文集具有更深层的学术价值。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马克·布洛赫的两卷本《历史文集》(Mélanges historiques)出版后,他在封建社会研究、社会学理论及历史比较方法等方面的思考才得以系统化呈现。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大漠丰碑》一书,同样让我们对作者四十年来的学术工作与事业有了整体性的认识,这便是笔者眼中解读《大漠丰碑》的三把“钥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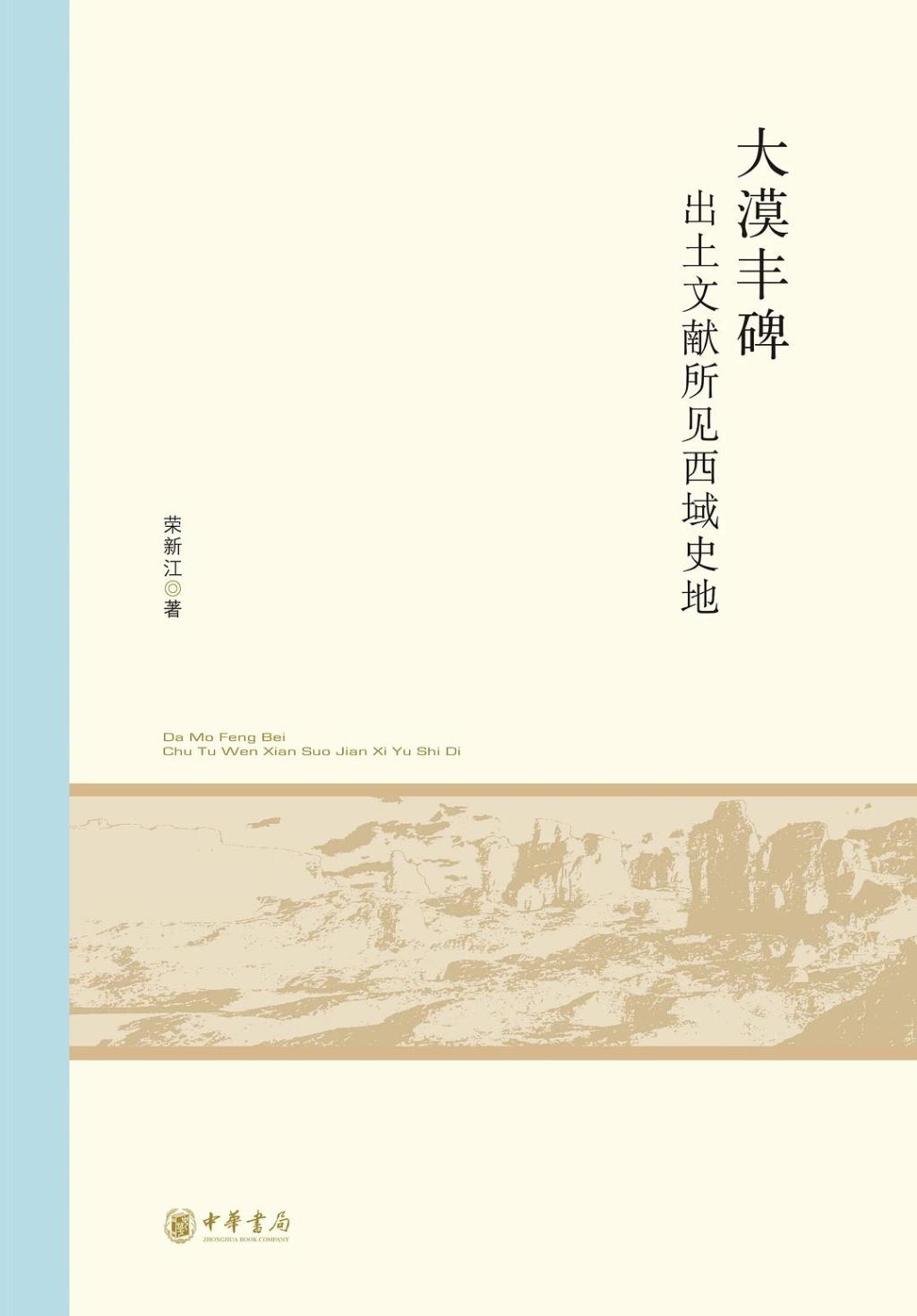
荣新江著《大漠丰碑:出土文献所见西域史地》
第一把钥匙是“西域历史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学术思想,它是串联本书中西域史地与边疆民族研究多篇论文的核心线索。这一思想最早的公开文字表达,是作者1985年7月30日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归义军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当时年仅二十五岁的作者在论文结语中提出“河西和西域的历史是诸民族共同创造的”,并进一步指出“在失去唐朝或吐蕃王国物资调配能力的情况下,各地方政权通过交换物品来补充自身并从中获利的中继贸易得以开展”,以及“当时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沙州、西州、于阗等地产生的佛教文献或艺术品,都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晶”。本书收录的《小月氏考》《龙家考》《通颊考》《唐代河西地区铁勒部落的入居及其消亡》四篇早期论文,都与作者的硕士论文密切相关。尽管这四篇论文的酝酿、撰写、修订和发表时间跨度十余年,但综合来看,能清晰看到其中统一且连贯的思想。例如,作者研究小月氏时,没有像蒲立本、榎一雄那样从民族迁徙角度探讨其踪迹,而是从民族融合的视角考察小月氏的演变;对龙家、通颊及入居河西的铁勒的追溯,也着重考察他们融入当地的历史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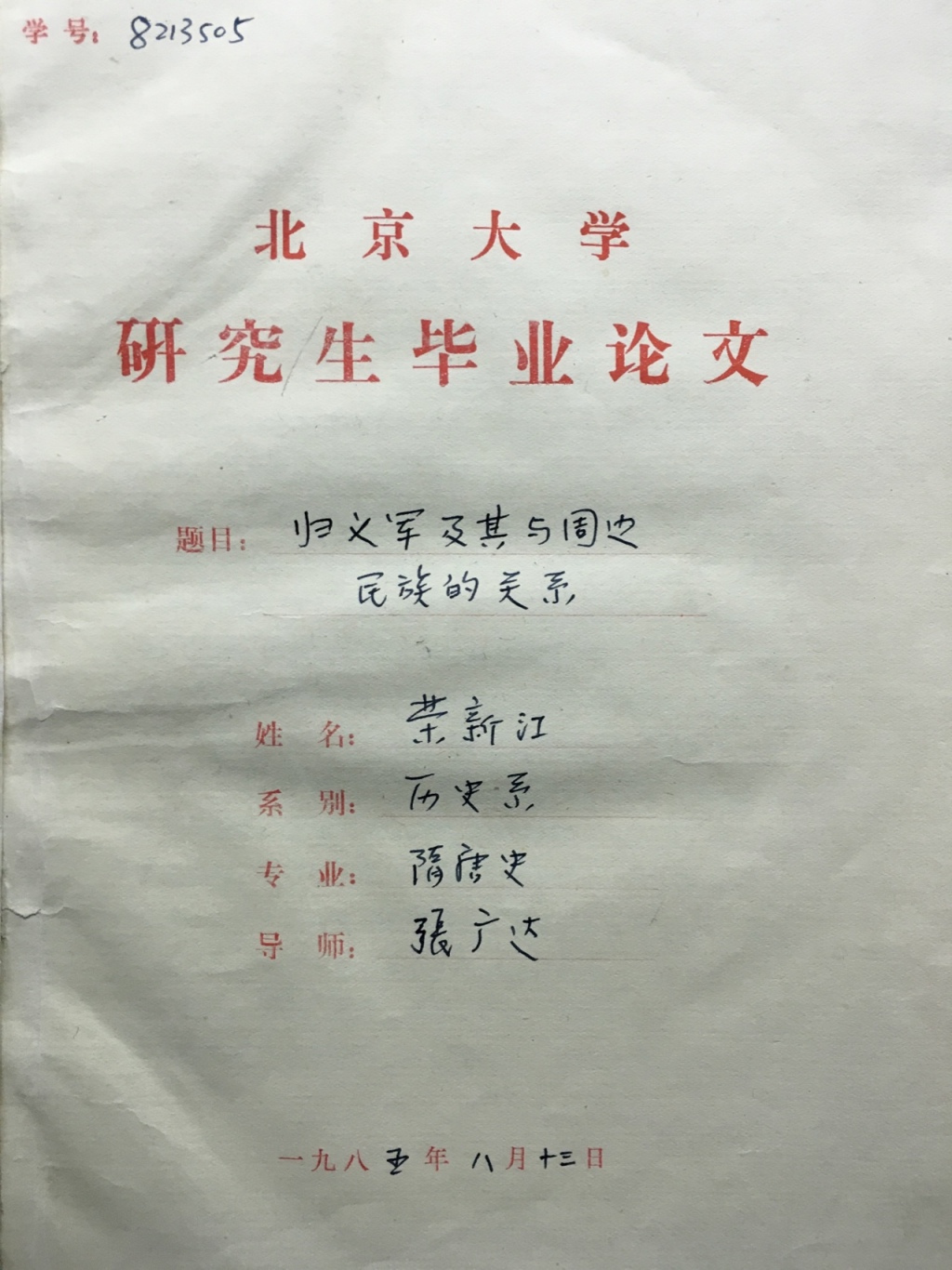
荣新江硕士学位论文封面
沿着“西域历史共同创造说”继续阅读,我们能串联起本书中其他多篇论文或词条。《所谓“吐火罗语”名称再议》解释了龟兹北庭间的“吐火罗”如何在高昌回鹘与当地说印欧语的胡人间的互动中“产生”;《唐贞观初年张弼出使西域与丝路交通》《大中十年唐朝遣使册立回鹘史事新证》挖掘出两位在历史中湮没的唐朝使者出使西域的事迹;《从新出墓志看入唐西域人的活动——以哥逻禄炽俟家族为中心》考察了说突厥语的炽俟家族从西域到长安的迁徙与生活轨迹(有趣的是,一方墓志的志主炽俟弘福正是本书收录的《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唐龙朔年间哥逻禄部落破散问题》一文中炽俟步失的孙子);《“西域”概念的变化与唐朝“边境”的西移》展现了唐朝对西域的成功经营,尤其是安西四镇的开拓,使当时人们的“西域”观念悄然改变;利用出土文献和文物论述于阗与敦煌两座绿洲城市间文化交流的两篇论文及“裴矩”“王玄策”两个人物词条,实际上都是对参与创造西域历史者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由“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个词条修订合编而成的《西域绿洲王国简史》,这四个词条首先列出不同语言的人群对该地的称呼,并注重综合运用汉文史料和于阗语《佛本生赞》、焉耆语《弥勒会见记》、出身疏勒的优素福·哈吉甫创作的《福乐智慧》等当地非汉文材料来论述四地的历史文化。
第二把钥匙是打破文明交流研究中物质交流与文化交流之间的壁垒,转而分析两种交流互动过程的框架性理论。《纸对佛典在西域传播的贡献》一文从佛典的书写载体切入,展现了一幅复杂宏大的文明交流图景:佛典早期的书写载体是沉重的桦树皮,因此其最初传入中原时依赖口头传授的方式;当中原纸张向西传入西域后,反过来推动了佛典的传播;不仅如此,作者还将纸张的传播与我们此前熟悉的一些史实联系起来,如魏晋至唐初的求法活动,以及《华严》《般若》《涅槃》等规模宏大的佛典传入中原。在已有的研究中,物质层面的纸张传播与文化层面的佛典传抄、译经求法等活动分属不同研究领域,前者为科技史研究者关注,后者则是佛教史的研究范畴。在中外关系史的一般叙述中,纸张传播和佛典传播也是分开讲述的两部分。然而,作者在纸张传播史与佛教文化传播史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为我们呈现出具有历史纵深感的复杂交流过程。20世纪量子力学研究兴起却引发物理学家更多困惑时,爱因斯坦曾指出:“理论决定了我们能观察到什么。”作者对“纸”与“佛典”传播的研究亦是如此,它为文明交流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典范性和可操作性的框架性理论,指引研究者在观察区域间或文明间交流时,关注物质与文化两个交流层面的联系与互动。

2005年荣新江在楼兰考察途中拍摄
第三把钥匙是作者发出中国声音、提升中国学术地位的事业及其背后的爱国主义精神。本书收录的《通颊考》等多篇论文以及《敦煌学十八讲》《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等论著早已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在此无需赘述。我想重点论述的是《所谓“图木舒克语”文书中的“gyāźdi-”》和《据史德语考》两篇论文的意义,它们在作者迄今发表的数百篇论文中似乎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位于新疆西部的图木舒克遗址出土了婆罗米文、吐火罗文、汉文、回鹘文等多种文字写成的文书,其中一类用婆罗米文书写的伊朗语曾困扰着研究者。1950年,贝利(H. W. Bailey)用地名“图木舒克”称呼该语言。1971年,恩默瑞克(E. R. Emmerick)首次使用“图木舒克语(Tumshuqese)”这一名称。然而,这种定名存在严重问题。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这种语言属于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中的东伊朗语分支,但“图木舒克(Tumshuq)”并非伊朗语词,而是突厥语词,且直到11世纪后期才出现,比该语言的使用时间晚了数个世纪,而且国际上命名古语言的通行做法是“名从主人”。因此,用一个突厥化的地名来命名一种更早的东伊朗语极不合适,说这种语言的人们绝不可能认为自己说的是“图木舒克语”。伊朗学家们之所以不假思索地采用这个有问题的称呼,甚至现在仍在使用,恐怕是因为他们认为没有必要考虑中国新疆某个区域的丰富历史,或是深入探究曾生活于此地的人们的想法。这些研究者对中国同行其实颇为友好。

1985年荣新江(中)前往剑桥拜访贝利(左)
在作者“满世界寻找敦煌”的旅程中,贝利、恩默瑞克都曾热情接待过他,后者还是《据史德语考》另一作者段晴教授的导师。但正是他们这种未曾深思的定名,更能说明欧美学界自殖民时代以来的“东方学”思维,即远在中国新疆的研究对象是一种凝固的抽象存在。因此,他们才用一个后起的地名随意地“覆盖”了之前据史德的历史。这些古语言的主人失去了自己的“名字”,他们所面临的境遇,正如萨义德(E. W. Said)援引马克思的名言对“东方”的评论——“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达”。事实上,这种境遇也是20世纪敦煌学和西域史地学术史的一个隐喻。近代以来,英、法、德、俄、日等国的探险队先后来到中国,劫掠了敦煌、吐鲁番、和田等地出土的大批文物。随后这些国家又以各自掠夺的文物为基础,积累了丰厚的学术成果。这种在资料和研究上的双重困境,正是中国学者曾经不得不面对的不利局面。20世纪初,罗振玉等学者研究敦煌文书依赖伯希和(P. Pelliot)携带的写卷;20世纪末,日本学者曾自夸“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陈寅恪曾哀叹:“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只有置于这样的学术语境中,这两篇论文才能彰显其真正的意义。1991年发表在日本《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的《所谓“图木舒克语”文书中的“gyāźdi-”》,详细列举语言学和历史学证据,论证文书年代为唐朝控制塔里木盆地时期。通过梳理当地历史沿革,作者指出“图木舒克”就是唐代的据史德。最为重要的是,作者从这种语言写成的文书中检出“gyāźdi-”一词,并将其可信地比定为“据史德”;还检出藏文文献《僧伽伐弹那授记》中的Gus-tig来自汉文“据史德”作为佐证。作者与段晴教授合撰的《据史德语考》进一步从语言学和历史学两方面反驳了该语言为疏勒语的观点。尽管已刊布的据史德语文书仅有十五件,但曾生活在唐代西域据史德的人们,终于通过这些仅存的残片向后人宣告,他们与图木舒克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来自据史德:
jezdam-purā-ā xšande gyāźdiyā ride wāsudewā xšimane xšane śazdā sālye ahverjane māste bistyo dreyyo
神之子、统治者、尉头/据史德王世天在位第六年、蛇年Ahverjana月二十三日。
因此,《所谓“图木舒克语”文书中的“gyāźdi-”》和《据史德语考》两篇论文的意义,不仅是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声音,也是为埋藏在黄沙之下的人们摆脱“东方学”阴影的遮蔽,发出自己的“声音”。我认为,这两篇论文和本书收录的其他论文,乃至“满世界寻找敦煌”与整理刊布出土文献的事业,实际上都可以从这个意义来理解,而它们背后的共同根基是作者的拳拳爱国之心。
在跟随荣老师学习的过程中,有两件事让我印象深刻,或许能帮助读者对此有更深的理解。第一件事是我引用内田吟风等日本学者译注的《骑马民族史:正史北狄传》时,直接抄录出版年份为“昭和某年”而未换算成公元纪年。老师批注道:“怎么能用战犯的年号!”此事虽已过去十年,但写下时仍让我冷汗直流。第二件事是我参加工作后,某次和老师闲聊时提到,我在备课时注意到他不用社会上甚至学界最常见的“大英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来称呼“The British Museum”和“The British Library”,而是用直译的“英国博物馆”“英国图书馆”。荣老师淡然回答:“本来不就如此吗?”是啊,本来不就如此吗?但为何人们总像国外学者不假思索地使用“图木舒克语”一样,不假思索地使用“大英”二字呢?
仔细梳理近年历史学议题的更新,西域史地和边疆民族研究、中外关系史与文明交流研究吸引了学界内外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学界正逐渐尝试向世界发出更多声音。而这一切,其实都是作者在过去四十多年间投身的事业。也正因为如此,本书收录的新旧“预流”论文以及文字背后传达的思想、理论与精神这“三把钥匙”,在当下和未来将愈发显示出其价值。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版权归原创者所有,如需转载请在文中注明来源及作者名字。
免责声明:本文系转载编辑文章,仅作分享之用。如分享内容、图片侵犯到您的版权或非授权发布,请及时与我们联系进行审核处理或删除,您可以发送材料至邮箱:service@tojo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