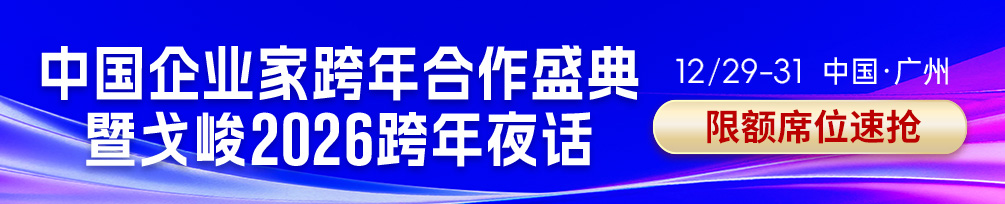在30平方米的无障碍酒吧里,我们将成见折叠并摊开
【编者按】
五月十五日是全球无障碍宣传日。
在上海的新华路上,有这么一个小酒吧。酒吧的高度和容膝深度考虑了坐轮椅的顾客。墙上的盲文标志和手语白板供视障和听障人士使用。它还建立了一个“结合”的空间和社区,让残疾人、残疾人和健康人相互看到,也延伸了我们对“无障碍”的认知——“无障碍”不仅是指物理设施,更为重要的是,让每一个人平等拥有自由舒展的空间,进入更近的关系,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
"除按摩店外,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聚会"
在一场户外开放的麦音乐会上,每个人都围坐在露营椅和轮椅旁,唱歌、听歌、聊天、喝酒。晚上唱歌的时候,“无碍理想”的店铺点亮了暖光。去年5月,这家酒馆在上海新华路创意园区举行了一场开幕式。经理玉杰看着轮椅伙伴们使用店内无障碍设施,自然进出点餐。这是他多年来理想的场景。
十多年前,玉杰上中学时左手功能意外受损。身为一位备受期待的“小镇做题者”,周围的人开始向他表达“遗憾”。青春期的他,内心的孤独与迷茫交织在一起:自己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社会角色?能否融入一个群体,进入更近的关系?他觉得身边健康的人不能和他有深刻的理解。在网上,他发现中国有大量的残疾人,而生活中几乎没有其他残疾人,他一直很困惑。
根据公开报道,我国约有8500万残疾人,相当于每16人中就有一名残疾人。
玉杰后考入中国政法大学,并获得奖学金前往美国深造。在美国,他观察到无障碍设施在各种公共场所非常受欢迎——据他所知,上个世纪美国修订的《残疾人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ADA)和《508法案》(Rehabilitation Act Section 508)等法律法规共同推进了无障碍环境建设,并确保残疾人能够平等地获取信息和服务。在校园里,他还开始和患有听力障碍或坐轮椅的同学一起上课。他还开始在校园里和患有听力障碍或坐轮椅的学生一起上课。接触之后,玉杰发现自己生活中遇到的障碍比自己多,难以处理。
为了缓解学业压力,在美国深造时,法学院每周四晚上都会组织学生在附近的街角酒馆聚会。这些喝酒的社交时间让玉杰得到了很好的放松。然而,在这样的地方,他仍然看不到残疾学生。
现在他和搭档小美给了一家酒馆,提供了中低度的“微醺”自酿啤酒,更重要的是大家休息时间的社会属性——玉杰想在消费模式中建立一个无障碍、多元化的公共空间:“首先,我们必须有一个共同的领域,一个看到彼此的机会。”

玉杰正在喝酒。
这里的位置是看中新华社区的氛围——周边有一个深耕多年的社区建设组织——上海大鱼社区建设发展中心;因为店铺位于一楼平地,也是毛胚房,所以可以改造的空间很大。然而,玉杰和小美前后问了十几家商业室内设计公司,他们都说没有无障碍设施经验。他说:“这不是一种高科技的设计,但是需要从体验者的角度来考虑。比如为轮椅搭档设计的吧台,除了桌面高度之外,还要考虑容膝容脚空间等细节。 (深度不低于25cm)。”玉杰在几次不同障碍的其他群聊中选择了他们对无障碍设施的需求,然后将这些建议反馈给设计师。
最终,在不到30平方米的空间里,有各种各样的细节供残疾人考虑。入口扩大并采用带扶手的折叠侧开门,轮椅用户进出时可单手开关。室内吧台有高低组合;白板上有一张简单的手语科普图,供聋人和听众写作和交流;墙上盲文版的室内图,方便视障人士了解整体室内布局。只是公园里还没有无障碍厕所,伙伴们就会到隔壁巷子里的“大鱼创造”上厕所,那里的入口台阶铺上渡板。玉杰还邀请设计师为园区制定计划,试图促进厕所改造。

手语科普在酒馆一角。
小米,一个在新华街区出生长大的居民,带着视障朋友毛毛坐着轮椅来参加酒吧的开幕式。他们去年在“大鱼创造”活动中相遇,早些时候一起参加了周围的无障碍活动。来到公园口,毛毛听到热闹的吉他弹唱声,原本犯困不想来的他立刻变得明亮起来。小美把酒馆的布局介绍给毛毛,带他在屋里摸了摸:打酒机在哪里,桌子是什么样子,还有盲文版的室内布局——毛毛高兴地发现,这是根据他两天前在酒馆群聊中提出的建议制作的——小米当时把毛毛拉进群聊,毛毛发现群里有很多在其他网络社区认识的积极合作伙伴,说话一直很积极。每个人都在讨论这张布局图,玉杰前后发了五六版修改图,毛毛建议去掉一些多余的空格和符号,更符合盲人的阅读习惯。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直接打印了布局图。

在酒馆里,毛毛(右一)参加活动。
小米记得去年年初和几个坐轮椅的伙伴一起参加一个无障碍活动后,一起吃饭的时候聊到了残疾人的各种需求。谈论去酒吧喝酒和社交也是一种——但是因为缺乏无障碍设施,他们根本进不去;有些朋友的家人会教他们酒吧是个“坏地方”。没想到,半年后,他们的想法在这里完成了。
之后,毛毛还带着两个来自北京的视障朋友来到酒吧。那天三个人在一起聊得很开心,朋友的话给毛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按摩店,我们还有另一个聚会的地方。”
程菲菲也和她的朋友一起去了商店。那天晚上,她遇到了几个从事艺术工作的听众。当她得知自己聋了,他们试图用肢体语言与她交流,这让她感到非常放松。
手语是程菲菲的第一语言。在日常生活中,当她遇到一个听不懂手语的人时,她会耐心地用文字交流。但很多时候,对方要么不知所措,要么不理他们就走了。
毕业后,程菲菲进入一家社会企业进行手语教学和文化传媒。有一次,她和两个听众约好在酒馆策划手语教学活动——之所以约好在酒馆,是因为程菲菲之前没有去过酒吧,她很好奇——但那一次,她感觉很糟糕:他们通过语音立即转换文字的App进行了交流,因为酒吧里人很吵,文字识别一直受到影响。更重要的是,程菲菲没有感到被尊重:“我坐在他们中间,看着他们一直张着嘴说着什么,我就像一个气体;他们也有一种感觉,他们在做决定,而不是残疾人。”程菲菲当时并没有表达自己的不满,后来发了一条信息和对方的解释,他们才意识到。
每次程菲菲来到这里,她都会遇到小米,咧着嘴笑着和她打招呼——小米住得很近。虽然她没有喝酒的习惯,但她每周会来这家酒馆三四次。程菲菲在这里遇到的很多听众都不会说手语,但是和她交流的时候,他们会努力比较画面,真的不能再打字发消息了。
程菲菲发现主理小美也逐渐学会了一些基本的手语:“你好”、“谢谢”、 "我需要帮助吗?"、“你想喝什么”等等。“小美曾经告诉我,她认为手语很美。听力和聋人的区别在于语言的不同,而不是听力——我同意这句话。”程菲菲说。
每个人都关心如何参与其中。
去年6月,程菲菲得知“无碍理想”正在招募“一日主理人”,她鼓足勇气向玉杰提出了举办手语活动的想法,并立即得到了支持。于是,程菲菲与手语教师、手语翻译一起,对听众进行了日常手语教学,普及了聋人相关常识。举例来说,正确的称呼应该是“聋人”、“听障人士”,而不是“聋哑人”——这个词是歧视性的。事实上,大多数聋人的喉咙都没有问题。由于身体素质、家庭教育和学校环境的差异,一些聋人可以听到一点,说一点英语口语。虽然有些听不见,但他们的英语口语很清楚。
去年9月底,在酒馆的“国际聋人周”系列活动中,程菲菲设置了一个摊位游戏,模仿表情,测试视力和手速:让聋人和听众在笑声之间增进对彼此的了解。毛毛也来到了现场,发现没有办法参加。之后,程菲菲加了毛毛微信,问他觉得盲人怎么能参加这样的活动。
几个月后,程菲菲和听人朋友木木一起在酒馆举办了手语版狼人杀戮游戏之夜。现场有手语翻译做聋人、听人之间的桥梁,还特意请了一位手语语言学研究生为毛毛做口述者。口述者一直坐在毛毛旁边,在最初的手语教学阶段,她会边说边教毛毛比画手语单词。进入游戏后,口述者会告诉毛毛现在是几个玩家在说话;哪个玩家用手指着谁,他实际上在说什么——这些都是看不见的细节。这一次,毛毛的感觉是“完美”的,活动结束后,他和程菲菲说,如果自己再好学一些手语,就可以更多地与大家互动。

主持手语版狼人杀戮活动的菲菲(左三)。
毛毛喜欢这种新的体验:“以前我觉得盲人就是盲人,聋人就是聋人,但是在这里我发现不同的群体可以一起交流。”
有一次,毛毛在酒吧的帮助下,在几个地方刻上了盲文标志:酒吧、啤酒墙和折叠桌。小美顺势问毛毛:“你想教大家盲文吗?”毛毛有点胆小:“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小美鼓励他:“有了这些盲文标志,大家可能都会对盲文感兴趣。”
就这样,毛毛策划发起了第一场盲文科普活动,小美做了一张活动海报。毛毛去问玉杰和小美,因为他们不确定定价和活动流程。他们还会时不时问毛毛:“你怎么想呢?”“你认为这可以吗?”
活动当天,毛毛介绍了盲人按摩和计算机屏幕阅读软件的历史,并带你用活动前选择的废弃塑料瓶盖拼出盲人版本的字母名称。“我希望盲人文本不仅会出现在教材中,而且会被更多的人理解。”十几个观众中,有的拍纪录片,有的做无障碍设施。
在毛毛后办的车间里,他引导参与者戴上眼罩,在酒吧里感受黑酒,分享自己的成长经历。科普一些无障碍设施的具体情况:比如带盲文按钮的电梯,其实对于视障人士来说是不够方便的,因为它通常缺乏“到达哪个楼层”的语音提醒;对于带盲文的电脑键盘,这个设计其实很累赘——键盘上盲文的凸起点太多,影响打字触感。对于盲人来说,键盘只需要f、两个凸起的定位就足够了。
在毛毛和家人看电视之前,他们刚刚播出了关于盲人的报道。父母对毛毛说:“看看别人有多厉害!”毛毛的第一个想法是和他们争论:“现在媒体上有两个极端的残疾报道,要么特别励志,要么特别惨。我们和健康的人一样平等。”
毛毛老在山西老家县说“无障碍”、“结合”这些词,但是这些词到底意味着什么,他实际上并不十分清楚。2011年,毛毛16岁时,有团队开发了国内首款免费读屏软件,这是毛毛首次听到“信息无障碍”的概念。随后在家乡按摩店工作,他认为能够适应社会就是无障碍。两年多前,父母说要租房子给他开店,催他找对象结婚。他抓住了一家公益机构做AI培训的机会,来到了上海。他觉得自己可以走出按摩店,像其他人一样工作,有收入,这是无障碍的。接触到“无碍理想”酒馆后,毛毛现在觉得,“无障碍”就是要学会尊重大家的想法,共同创造一些东西。几次活动练习让他明白,“无障碍”并非一句口号,而是一些小细节慢慢地从实际中聚集起来。
对于经理玉杰来说,“每天在酒馆里的感觉都不一样”。玉杰说,自从中学左手受伤后,他实际上已经适应了自己的身体。现在在酒馆里日复一日地打酒、洗杯、拖地,他发现自己也能把这些小事做好。他觉得,“结合、同创”并不是“激励”别人做事,而是“信任”别人,“抑制”自己不要过多干涉。小到酒馆角落里一个杯子里的助听器电池:“是一位聋人熟客小吴捐赠的。从她的角度来看,她愿意为这个空间做贡献。”
向所有人敞开
无障碍理想的在线群聊早已满员,残疾人和完美人士各有一半。每天的演讲和讨论都很活跃: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无障碍资源和活动分享,也有生活琐事的插科打诨。
不久前,毛毛在群里@小米“生日快乐”,大家纷纷发帖:“米店长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冷笑话之王!”看到一排排的祝福,小米不时感谢:“我给你一个!”“我在后面翻了一个!”那天晚上,小米和店里的每个人分享了生日蛋糕。墙上挂着一张印有他照片的长长祝福海报:“1%的小米让我们看到了100%的生活。”
“我想舔狗,或者只是觉得无聊的时候就去聊天。”小米住得很近,早就让玉杰拿酒吧钥匙,下午经常提前进店帮忙做一些晚上营业前的准备。他在这里学会了喝酒和煮热红酒,这是他以前从未尝试过的。客人多的时候也帮忙接待,开着轮椅到处走,用活泼随和的性格优势和大家混在一起,于是被大家嘲笑为“米店长”。

小米在酒馆帮忙整理。
虽然毛毛住在浦东很远的地方,但是除了办活动之外,他每周都会来酒吧坐一坐。有一次在酒馆里,毛毛和一个来自苏州的盲人及其女友聊了几个小时,然后一起坐地铁。毛毛知道女孩可以看见,但是一路上她的声音是从离他较远、较低的位置传来的,他一问才知道对方是轮椅用户。毛毛谈到平时走在路上总会有人问他:“你怎么一个人出来,你的家人?但在“无碍理想”中,他觉得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会知道对方是否残疾,只要找到一个有趣的话题就可以交流。”
从地铁站到酒馆有一公里的路。起初,毛毛不好意思表示,独自走这条路对他来说并不那么方便——路会经过一个路口。和上海大部分红绿灯一样,这里没有声音提醒;手机导航有时会提醒毛毛“红灯40秒变绿”,但以后就没声音了。许多时候毛毛只能等着在路口用心听车的声音,或者等着路人来问:现在可以过马路,是红灯还是绿灯?
有一天,他向小美表达了这个困惑:“你能叫人来地铁站接我吗?”小美对他说:“没关系。你可以说出你的想法。”之后,毛毛直接在群里问:今天有没有人一起参加这个活动?如果你也坐地铁,我们可以一起来。
还有一件事,毛毛也发现了自己身上的变化。由于结识的伙伴越来越多,每次毛毛来到新华街区,都会有人跟他打招呼,有时候对方会问毛毛是否认出了他的声音。实际上,毛毛并不一定能记住每一个人:“盲人在生活中使用更多的听觉,但并不意味着盲人的听觉一定特别敏感。”有一次,他在群聊中分享了这一困惑,得到了理解的回应:“大家都告诉我,这件事不会太在意。”如果他现在认不出对方,就直接说:“我也有听不见的时候。”
小阳,一个住在附近的居民,因为去年在《新华录》的主编中担任非营利性地方生活,对酒馆产生了依恋。编辑部经常在创作的几个月里去酒馆开会。毛毛和小米都是编辑团队的一员。他们一起讨论,在杂志上增加了无障碍科普板块。杂志上所有的照片都是由听障人士小凡拍摄的。酒馆里多样化的融合感吸引着晓阳:有时他看到一桌伙伴的轮椅在旁边排除,旁边一桌聋人在玩纸牌游戏UNO。晓阳发现许多残疾人性格温暖,和他们一起喝High会互相开玩笑,兴之所到大家都会到门前的白板上涂鸦。
杂志已经编好了,酒吧已经成为晓阳生活的一部分。遇到晓阳的那天,他下午带朋友去酒吧聊天,回家吃饭,带老婆女儿去酒吧坐了一会儿。对于辞职后待岗的他来说,这是一个“带着一点理想乌托邦”的出现。

酒吧里的照片墙。
与晓阳不同,Edwin并不是酒馆的常客,但是进门后很快就和几个聋人打了手语,看起来很熟悉。之后我跟他聊天才知道,2007年他上大学的时候去韩国交换,是在一所基督教学校,里面有很多残疾学生。在他的三个室友中,有两个聋人,环境让他在生活中慢慢地学会了手语,“否则不能与外界交流,我会很孤单”。下课坐电梯的时候,经常会遇到几个用轮椅的同学。Edwin不得不排队等更多的电梯——在韩国的那一年, Edwin 体验健康人作为少数人的感觉。
去年夏天,他承受着巨大的创业压力,当他放松的时候,他在这里偶然遇到了这个地方。那天,一个聋人接待了他。多年后,他用熟悉的手语说话。他觉得手语是一种表达形式,不用上专业课才能学会,但学了之后也不会轻易忘记。那天他在酒吧看了很久墙上大家的照片,心里放松了很多。他每隔几个月就来一次。
Edwin和我聊天的时候用了“聋哑人”这个词。小米听到了,转过头说:“我得纠正这个。我们不谈‘聋哑人’,只谈‘聋哑人’或‘听障人士’。”
哦,是的,是的,是的。”Edwin迅速改正。
小米提醒我,这里不是“残疾人酒吧”,每个人都可以来,而是“一个喝得微醺,享受快乐和归属感的地方”。
(文中人物小美、毛毛、小米、Edwin为化名,以保护受访者的隐私。)
设计 白浪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版权归原创者所有,如需转载请在文中注明来源及作者名字。
免责声明:本文系转载编辑文章,仅作分享之用。如分享内容、图片侵犯到您的版权或非授权发布,请及时与我们联系进行审核处理或删除,您可以发送材料至邮箱:service@tojo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