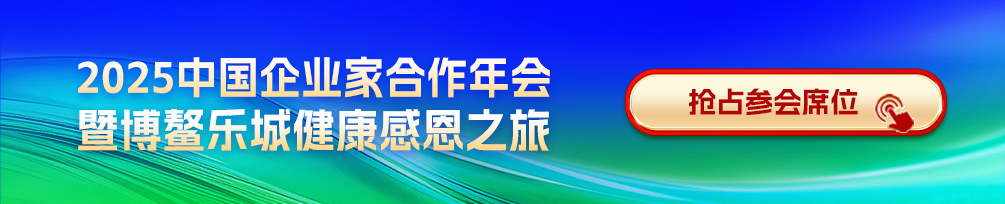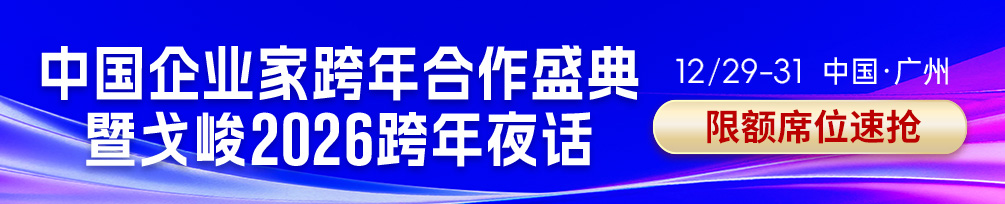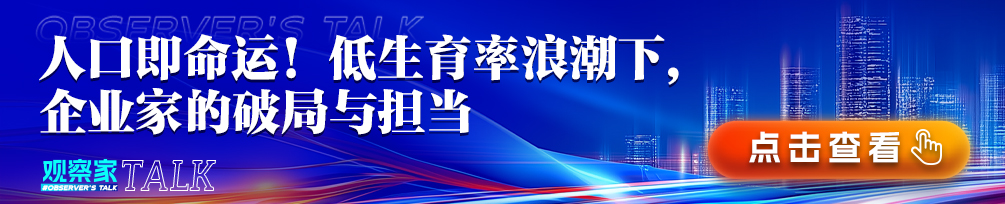回顾人类史上“最致命疫情” 历史会重演吗?
来源丨叶檀财经(ID:tancaijing)
作者丨燕十三
今年是新冠肆虐的第三个年头,我们为长三角等地担忧,但又对未来抱有希望。
在人类近现代历史上,因为还没有哪一种此类病毒度过了“三年之痒”,这种矛盾的心态充斥在各个地方,从防疫政策到社会舆论,从传统报刊到网络社区。
如果把人类社会当做一个大型的培养皿,把防疫政策的不同当做浓度不同的营养物质,然后从专业生物实验和历史回顾的力度去思考上述,可以得出很多值得思考的结论。
首先,中世纪肆虐的天花、牛瘟病毒,包括前些天被发现传播的猴痘病毒,基本是DNA病毒。
这类病毒虽然毒力惊人、杀伤性强大,但遗传物质变异缓慢,疫苗和药品很容易对症下药,所以反而在近现代社会中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
而现代社会的“顽固”病毒品种,基本是RNA病毒,如艾滋病毒、流感病毒、禽流感病毒、新冠病毒,这类病毒毒力相对较弱,但传染性和遗传物质变异速度惊人。
譬如流感病毒,从1918年被发现到现在已经过了100年,但仍旧时常“焕发新生”,2010年肆虐中东、南亚的甲型流感H1N1病毒就是例子。

二者的区别恰如急性病和慢性病。
慢性病在全球医保支付中占据绝对优势,比如2021年全球慢性病管理的市场规模就接近4500-5000亿,约占全球医疗费用总开支的1/4。
回顾1918-1920年西班牙大流感,当时既无疫苗,口服特效药“达菲”要等到80年以后,但最终“有惊无险”。
从1918年3月也就是春天,在美国堪萨斯州军营发现首例流感病毒开始,到1918年9月也就是秋天,在美国波士顿军营,发现第二个变异品种,其毒力持平但传染性剧增。
随后病毒被参战美军带到西欧,参战双方缠绵病床的感染士兵一度超过百万,并导致当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英法和德国都把精力从战争转向严峻的防疫。
然后到1919年10月,又是一个秋天,病毒进化出第三个品种,传染性继续飙升,但致死率快速下降至万分之一(预估)以内,来年各国就宣布抗疫结束,虽然病毒还存在,但已经不足以威胁人类社会安全。
RNA病毒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的变异是无穷无尽的,也很难有两个完全相同的RNA病毒,但我们这里只将有“统治力”的变异品种纳入思考,比如德尔塔、奥密克戎以及可能出现的下一个变异品种。
其次,新冠病毒和西班牙大流感的“经历”是高度雷同的。
从2019年12年发现首例病毒,毒力较强,传染性一般;
到2021年5月世卫组织在印度发现了第二个变异品种德尔塔毒株,毒力持平,但传染性大幅增强(考虑到2020年10月印度当地就有类似的症状出现,大概率是在秋冬季节开始传播的);
然后是2021年11月在南非发现的奥密克戎毒株,毒力大幅削弱但传染性飙升(考虑到南非当地松散的防疫体制,参考印度的经验,病毒大概率是在2-3个月或者更早前就开始传播)。
可以发现,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病毒在经过三次变异后,致死率下降到了可以接受的水平,新冠病毒已经经过了两次变异,变异的方向也高度一致。
疫情初期,病毒被各国严防死守,这个时候疫苗接种人数比较低,人群缺乏对陌生病毒的免疫能力,此时病毒在毒力方面的变异对传播影响不大,不管是毒力上升还是下降,都改变不了各国严防死守的态度。
所以病毒的变异就只剩下提高传染性一条路,可以称之为“硬突破”。
“硬突破”后,正如德尔塔取代原始毒株肆虐世界,病毒的敌人就变成了“同行”,即传播能力更强的毒株。
突破了人类的防疫体制后,病毒回归了它本来的变异方向,因为病毒的目的并非消灭人类,而是和人类共存,人类DNA中大量的病毒基因残留就是例子。
此时此刻,病毒中谁的传播能力更强,谁就能够“占领”人类,至于毒性则成为了非必要选项,除非毒性低到人类可以在短时间内自愈。
这条路径,我们可以称之为“流感化”,也可以称之为RNA病毒的“进化之路”。
最后,病毒存在明显的“游牧民族”特征,夏天收缩甚至沉寂,秋冬开始传播,然后在春天大面积扩散。
任何种类的病毒,本质上是蛋白质壳包裹遗传物质,既然是蛋白质,就会随温度和紫外线影响“变质”,所以任何病毒的抗热性都不应高估。
虽然研究者常用德尔塔和奥密克戎在当地夏初发现作为反驳案例,但各方证据都证明,变异病毒在几个月前的冬天就开始传播,南非和印度的防疫体制也不具备在传播初期及时发现病毒的能力。
某种意义上,夏天是任何病毒的生死劫,2002年11月非典病毒在中国广东发现首例传染病例,在来年即2003年春天,非典病毒先后传播全国与全球各地,但该病毒抗热性极差,在2003年夏天就自动消失在人类视野。
但夏天也是病毒变异的“温床”,在严峻的传播环境下和大量的毒株死亡中,才有可能变异出最“凶猛”的品种,所以各类主流RNA病毒基本保持“每年秋冬上市一款新产品”的节奏:在夏天锻炼出最凶残的毒株,然后在温度转冷、紫外线转弱时开始传播。
新冠病毒的原始毒株R0在2-3之间,德尔塔毒株的R0提高到了4-5,而奥密克戎的R0值则到了7-8。考虑到病毒传染性在人类社交网络的加持上,会呈指数变化,也就是说R0差一点,在传播中感染人数可能会差几倍,最终所有的潜在感染者都会被高传染性的病毒变种占领。
在尊重科学的基础上推演未来,在未来的2-3月,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疫情的尘埃落定甚至销声匿迹。
在今年的秋天或者晚些时候,我们大概率能够看到一款毒力更弱但传染性更强的新冠变异“产品”。
过分悲观和乐观都是不可取的,重要的是尊重科学和常识,以史为鉴。
版权说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版权归原创者所有。部分图片源自网络,未能核实归属。本文仅为分享,不为商业用途。若错标或侵权,请与我们联系删除。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版权归原创者所有,如需转载请在文中注明来源及作者名字。
免责声明:本文系转载编辑文章,仅作分享之用。如分享内容、图片侵犯到您的版权或非授权发布,请及时与我们联系进行审核处理或删除,您可以发送材料至邮箱:service@tojoy.com